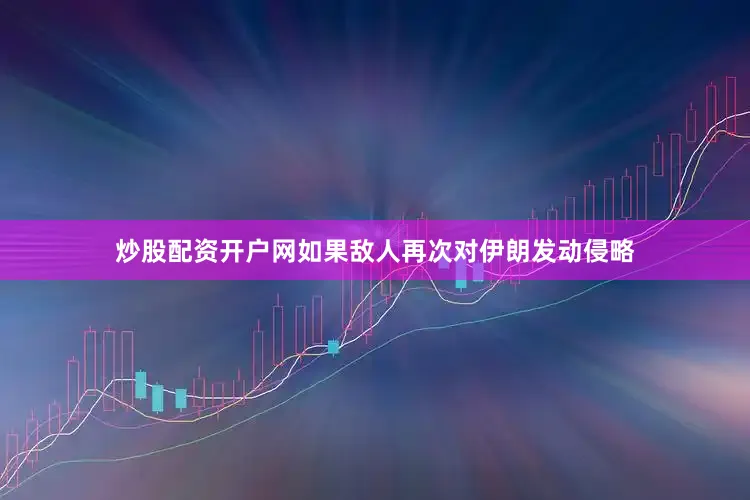“放着安稳日子不过,你图啥啊!”
父亲的怒吼还未散去,我却被一通军区密电,带到了上级领导面前。
“林霄然,我问你,”他目光如炬,语气无比严肃,“你知道你豁出命去救的那个人,她到底是谁吗?”
一句话,将我彻底问懵,也让我明白,那场风雪中的生死营救,远没有结束。

01
1992年,秋。
我叫林霄然,二十四岁,提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行李包,站在了阔别五年的家门口。
包里装着我的全部家当,一套叠得像豆腐块的旧军装,几件便服,还有一张转业证明。
空气里飘着一股煤烟和酸菜混合的味道,这是我们这座北方小城独有的味道,廉价,又充满了人间烟火气。
父亲正蹲在门口,用一根小木棍捅着炉子,煤烟呛得他不停咳嗽,背驼得像村口那座石拱桥。
“爸,我回来了。”我开口,声音有些干涩。
父亲猛地回过头,浑浊的眼睛看了我半天,才认出我来,他手里的木棍“啪”地一声掉在地上。
“霄然?你个臭小子,回来咋不提前打个电报!”他咧开嘴笑,脸上的皱纹像风干的橘子皮。
我妈闻声从屋里跑出来,围裙上还沾着面粉,她什么话也没说,就是拉着我的胳膊,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。
“回来就好,回来就好。”她翻来覆去就是这一句话。
家还是那个家,两间小平房,院子里堆着杂物,墙角那棵老槐树,叶子已经黄了一半。
晚饭是猪肉炖粉条,我妈把家里留着过年才舍得吃的肉都给炖了。
饭桌上,我爸一杯接一杯地喝着劣质白酒,脸喝得通红。
“在部队待了五年,人看着结实多了。”他拍着我的肩膀,眼神里是掩不住的骄傲。
“那是,咱霄然可是去保家卫国的,能不结实吗。”我妈在一旁给我夹菜,碗里的菜堆成了小山。
“对了霄然,部队咋样啊?是不是天天都真枪实弹地干?”我那个刚上初中的小侄子,满眼都是崇拜。
我笑了笑,不知道该怎么跟他们说。
我该怎么说,说那里的天比我们这儿的蓝,但风也比我们这儿的刀子还硬。
我该怎么说,说我们每天都在训练,汗水浸透的衣服能拧出水来,但更多的时候,是面对着无边无际的荒原和沉默的群山,忍受着足以把人逼疯的孤寂。
我只能含糊地告诉他们,部队很好,锻炼人。
“转业了,有啥打算没?”我爸喝了口酒,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。
“还没想好,先歇歇吧。”我说。
“也是,是该好好歇歇。”我妈心疼地看着我,“这几年肯定吃了不少苦。”
“苦啥,当兵的光荣。”我爸一瞪眼,“霄然,转业金可得收好了,那是你的血汗钱,留着将来娶媳妇用。”
我没说话,只是默默地扒着饭。
我知道,他们想问的,是转业金有多少,是部队有没有给安排工作。
在这个靠着一座煤矿过活的小城里,一份稳定的工作,比什么都重要。
可我,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头兵,能有什么安排。
那点转业金,在这座小城里,或许能盖个新房,娶个媳妇,然后就像我爸一样,一辈子守着这个家,慢慢老去。
这似乎就是我看得见的,未来的人生。
吃完饭,我妈拿出她给我准备的新被褥,上面有太阳晒过的味道。
“霄然,早点睡吧,明天我托你二姨给你问问,看看矿上后勤还缺不缺人。”
“嗯。”我应了一声。
躺在坚实的木板床上,我却翻来覆去地睡不着。
耳边没有了熟悉的紧急集合哨,没有了战友们粗重的呼吸声,安静得让我有些心慌。
我睁着眼,看着天花板,五年军旅生涯的一幕幕,像放电影一样在脑海里闪过。
那些汗水,那些伤痛,那些在巡逻路上的歌声,那些在大雪封山的日子里分着吃一个罐头的兄弟。
还有……那张在风雪中冻得发白,却依旧倔强的脸。
我叹了口气,把头蒙进了被子里。
都过去了,林霄然,别想了。
从今往后,你只是一个普通人,一个等着进矿上烧锅炉的转业兵。
02
让我无法入睡的那张脸,属于一个叫张诺伊的女军医。
遇见她,是在我退伍前的最后一个冬天。
我们驻守的地方,在边疆的无人区,人称“生命禁区”。
那里一年有八个月都在下雪,风刮起来,能把人吹个跟头。
我们的任务,就是守着那条长长的边境线,日复一日地巡逻。
那天,是我和老班长赵大海一起执勤。
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雪,但我们接到的命令,是必须去七号哨点检查线路。
七号哨点最远,也最险,来回一趟要大半天。
出发的时候,天还只是阴沉沉的,可没走多远,风就起来了。
那风跟狼嚎似的,卷着雪粒子,打在脸上生疼。
能见度变得极低,五米之外就看不见人影了。
我和老班长顶着风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。
“霄然,跟紧了!千万别掉队!”老班长在前面吼道。
“知道了,班长!”我扯着嗓子回答。
等我们好不容易赶到七号哨点,两个人都快成了雪人。
线路是好的,我们检查完毕,准备返回。
可就在这时,风雪突然变得更大了。
天和地,仿佛被一块巨大的白布给罩住了,分不清方向。
“坏了,这雪下得邪乎,咱们得赶紧回去。”老班长的脸色很凝重。
我们不敢耽搁,立刻踏上了归途。
可没走多远,我们就发现,麻烦大了。
来时的脚印,已经被大雪完全覆盖,我们迷路了。
在这样的天气里迷路,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。
气温在急剧下降,我感觉自己的手脚都快要冻僵了。
老班长的嘴唇也冻得发紫,他把水壶递给我:“喝口热水,暖和暖和。”
水壶里的水,已经快要结冰了。
我们背靠着背,躲在一块岩石后面,节省着体力。

“班长,你说咱们……是不是要交代在这儿了?”我心里有些发毛。
“瞎说啥!”老班长瞪了我一眼,“咱们是军人,就算是死,也得死在冲锋的路上!不能在这儿当孬种!”
就在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,我隐约看到不远处的雪地里,好像有一个黑点。
“班长,你看那是什么?”我指着那个方向。
老班长眯着眼看了半天:“好像是……一个人?”
我们俩心里都是一惊。
这种鬼天气,怎么会有人?
我们互相搀扶着,朝着那个黑点艰难地挪过去。
走近了才看清,那是一个穿着白色军大衣的人,趴在雪地里,一动不动。
我们赶紧把她翻过来。
是个女同志,很年轻,脸冻得没有一丝血色,眉毛和睫毛上都挂着冰霜。
“是……是新来的张军医……”老班长认出了她。
张诺伊,是一个月前刚从军区总院调来的军医,听说是个高材生。
她平时话不多,总是安安静静的,没想到胆子这么大,敢一个人在这种天气里出来。
“她还有气!”我把手伸到她的鼻子下面,探到了一丝微弱的气息。
“快!想办法救人!”老班长当机立断。
我们把她架起来,想带她走。
可她浑身冰冷,已经失去了知觉。
暴风雪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,带着一个昏迷的人,我们根本走不远。
“霄然,你听我说。”老班长喘着粗气,“我在这里守着她,你想办法,无论如何,要走回营地去,搬救兵来!”
“不行!要走一起走!”我吼道。
“这是命令!”老班长的眼睛红了,“她是为了给牧民送药才被困的,我们不能让她死在这里!你年轻,体力比我好,你走出去的机会更大!”
我知道,老班长说的是对的。
他把身上所有的干粮和最后一壶热水都塞给了我。
“记住,朝南走!别停下!”
我看着他,重重地点了点头。
我脱下自己的大衣,盖在了张诺伊的身上。
然后,我一个人,冲进了那片白茫茫的风雪里。
我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,摔了多少个跟头。
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:走下去,一定要走下去!
当我终于看到营地灯光的时候,我再也支撑不住,一头栽倒在了雪地里。
03
等我再次醒来,人已经躺在了卫生队的病床上。
指导员和几个战友围在我的床边,他们的脸上,是劫后余生的庆幸。
“霄然,你小子,命真大!”
我挣扎着想坐起来,第一句话就是:“老班长和张军医呢?”
“放心吧,都救回来了,一个不少!”指导员按住我,“你小子立大功了!”
我这才松了一口气,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,又昏睡了过去。
后来我才知道,我昏迷了整整两天两夜。
老班长被找到的时候,为了给张诺伊挡风,半个身子都埋在了雪里,冻得不省人事。
张诺伊因为有我和老班长的两件大衣保护,情况稍好一些,但也是重度冻伤,引发了高烧。
我们三个人,都成了卫生队的重点保护对象。
老班长醒来后,被指导员一顿臭骂,骂他不要命。
他只是嘿嘿地笑,露出一口大黄牙。
我去看了张诺伊,她躺在病床上,脸色依旧苍白,但已经脱离了危险。
我站在门口,没敢进去。
那是我第一次,那么近地看她。
她真的很清秀,不像是在我们这种风沙漫天的地方待着的人。
后来,听卫生队的护士说,张军医是为了给山那边的牧民送急救药,才冒险出发的。
那家牧民的孩子突发急病,通讯又断了,她心急如焚,就一个人上路了。
这件事,部队里给了我们三个人通报表扬。
老班长荣立二等功,我荣立三等功。
张诺伊醒来后,恢复得很快。
她来找过我一次。
那天我正在操场上扫雪,她就站在我身后,安安静静地看着。
“林霄然。”她开口,声音还有些沙哑。
我回过头,看见了她。
她穿着干净的军装,身姿挺拔,眼神很亮,像雪后初晴的天空。
“谢谢你。”她说。
“不用谢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我有些局促,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。
“你的大衣,洗干净了还给你。”她说。
“哦,好。”
然后,就是一阵沉默。
我不知道该说什么,她似乎也不是个话多的人。
最后,还是她先开了口:“我过几天,就要调走了。”
“调走?去哪?”我下意识地问。

她的眼神黯淡了一下,随即又恢复了平静:“回总院,这边……不适合我。”
我“哦”了一声,心里没来由地有些失落。
那次见面之后,我再也没见过她。
这件事,就像投入湖里的一颗石子,起了点涟漪,然后很快就恢复了平静。
我的军旅生涯,也走到了尽头。
我选择了转业,回到了这个生我养我的小城。
04
我回家的第三天,我妈就托二姨给我安排了一次相亲。
对方是矿上子弟学校的一个老师,叫李娟。
见面的地点,在县城唯一一家像样点的西餐厅里。
李娟长得挺白净,戴着一副眼镜,看起来斯斯文文的。
她对我似乎还挺满意。
“听我妈说,你当了五年兵?真了不起。”她搅动着杯子里的咖啡。
“没什么了不起的,就是尽义务。”我有些不自在。
“转业了有什么打算吗?我爸是矿上办公室的主任,你要是想来矿上,我可以让他帮忙问问。”
她说话很直接,也很现实。
我知道,她看上的,不是我林霄然这个人,而是我“转业军人”这个身份,以及可能带来的稳定和保障。
这顿饭,我吃得味同嚼蜡。
回到家,我妈迫不及待地问我:“怎么样?那姑娘不错吧?人是老师,有文化,家里条件也好。”
“妈,我还不想考虑这个。”我打断了她。
“你这孩子,怎么就不开窍呢!”我妈急了,“你都二十四了,再不找,好的都被人挑走了!你还想挑啥样的?难道还想找个天仙不成?”
我无言以对,只能躲回自己屋里。
就在我以为,我的生活就要在这样无休止的催促和安排中进行下去时,一个电话,改变了一切。
那天下午,我正在院子里帮我爸劈柴,村委会的电话就打到了邻居家。
是找我的。
我拿起听筒,里面传来一个陌生又严肃的声音。
“请问,是林霄然同志吗?”
“我是,您是哪位?”
“这里是北方军区司令部,我是办公室的王干事。”
军区司令部?
我心里咯噔一下,握着听筒的手都收紧了。

“王干事您好,请问有什么事吗?”
“是这样,林霄然同志,有位上级领导要见你,请你明天上午九点,到市里的军招所来一趟。”
“上级领导?见我?”我彻底懵了。
我一个刚转业的大头兵,有什么资格让军区司令部的领导接见?
“是的,请你务必准时到。带上你的转业证明和身份证。”对方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“好……好的。”
挂了电话,我半天没回过神来。
我爸凑过来问:“谁啊?啥事啊?”
“部队的,说是有领导要见我。”
“领导见你?你小子是不是在部队犯啥事了?”我爸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。
“我能犯啥事!”我也很烦躁。
这件事,像一块石头,压在了我的心上。
第二天,我起了个大早,换上了我那身洗得笔挺的军装,踏上了去市里的公交车。
军招所,是个很严肃的地方。
门口有哨兵站岗,我说明来意,出示了证件,才被放了进去。
一个穿着便装,但气质干练的中年男人接待了我。
他自我介绍说姓周,把我带进了一间小会客室。
会客室里,已经有两个人了。
一个五十多岁,穿着一身没有军衔的旧军装,坐在主位上,面容清瘦,眼神却像鹰一样锐利,他从我进门开始,就一直在打量着我。
他身边,还坐着一个年轻的女人,也是一身便装,长相很普通,但坐姿笔挺,眼神冷静。
我心里有些打鼓,这阵仗,不像是一般的接见。
“林霄然同志,请坐。”姓周的干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我依言坐下,身体不自觉地挺得笔直。
那个女同志先开了口。
“林霄然同志,我们找你来,是想跟你核实一些情况。”她的声音很平稳,没有一丝波澜。
“请问。”
“你在7758部队服役五年,期间表现良好,荣立三等功一次,个人档案里,没有任何违纪记录,对吗?”
“对。”
“去年冬天,你在执行巡逻任务时,遭遇暴风雪,和班长赵大海一起,救助了当时被困的军医张诺伊同志,是吗?”
“是。”
我的心跳开始加速,原来,是为了这件事。
“把当时的情况,详细地,再复述一遍。”女同志说。
我压下心里的紧张,把那天的经历,一五一十地,原原本本地又说了一遍。
我说完之后,屋子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那位老领导和女同志交换了一个眼神,似乎对我的回答,还算满意。
女同志又接着问:“林霄然同志,你对张诺伊,了解多少?”
我想了一下,然后诚实地回答:“了解不多。只知道她是新调来的军医,很有才华。”
我的话说完,一直沉默不语的老领导,终于开了口。
他的身体微微前倾,那双锐利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,语气变得无比严肃。
“林霄然,我问你,你知道你豁出命去救的那个人,她到底是谁吗?”
05
老领导的这句话,像一道惊雷,在我耳边炸响。
我愣住了,大脑一片空白。
张诺伊的身份?她不就是一个军医吗?还能是谁?
难道她有什么特殊的背景?是哪位首长的女儿?
可这跟我一个已经转业的普通士兵,又有什么关系呢?
我看着老领导那双仿佛能洞穿一切的眼睛,心里忽然有了一个荒唐的猜测。
“首长,我……我不知道。”我艰难地回答。
老领导没有说话,他只是从随身的公文包里,拿出了一张照片,轻轻地放在了桌子上,推到了我的面前。
那是一张黑白的老照片,照片上,是一个穿着军装,笑容灿烂的年轻人。
他的眉眼,和桌子对面的这位老领导,有几分相似。
但更让我震惊的是,我认得他。
虽然只是在部队的荣誉室里见过他的照片,但我记得那张脸,记得那个名字。
“他是……孔繁森?”我几乎是脱口而出。
是的,照片上的人,正是在边疆因公殉职,被追授为“模范共产党员”的孔繁森。
他是所有驻边军人心中的英雄和楷模。
“他是我大哥。”老领导缓缓开口,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。
我彻底呆住了。
我面前这位看起来普通的老人,竟然是英雄孔繁森的亲弟弟?
他叫孔繁军。
“我大哥牺牲后,留下一个女儿,当时才刚满十岁。”孔繁军的目光,落在了那张照片上,充满了追忆,“那孩子,从小就倔,她说,她长大了,要去我大哥工作过的地方,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事业。”
我的心脏,开始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。
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,在我的脑海里成形。
“她大学考了医学院,毕业后,放弃了留在大城市大医院的机会,主动申请来了边疆。”
“为了不被人当成英雄的后代特殊照顾,她隐瞒了自己的身份,改了名字,以一个普通军医的身份,来到了你们部队。”
孔繁军抬起头,再次看向我。
“她的真名,叫孔清雪。张诺伊,是她母亲的姓。”
“她……她是孔繁森的女儿?”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。
“是。”孔繁军点了点头。
屋子里,安静得能听见我自己的心跳声。
我终于明白了。
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张诺伊那么神秘,为什么她会一个人冒着暴风雪去给牧民送药,为什么她会说“这边不适合我”。
因为她背负的,不仅仅是自己的理想,更是父亲的遗志。
而她的存在,本身就是一道光,太过耀眼,也太过危险。
“那次暴风雪之后,我们知道了这件事,万分后怕。”旁边那位姓周的干事开口解释道,“英雄的后代,如果在我们这里出了任何意外,我们都难辞其咎。所以,军区党委经过研究,决定立刻将她调回内地,并且是最高级别的密令。”
“所以,你们今天找我来……”我看向孔繁军。
“是来感谢你的。”孔繁军的语气很真诚,“霄然同志,我今天不是以上级领导的身份,而是作为一个长辈,一个叔叔,来感谢你。你救了我大哥唯一的血脉,你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根子。”
说着,他竟然站了起来,要向我敬礼。
我吓得“蹭”地一下也站了起来,连忙拦住他。
“首长,您可千万别这样!我当不起!我只是做了一个军人应该做的事情!换成任何一个战友,都会这么做的!”我急得脸都红了。
孔繁军看着我,欣慰地点了点头。
“好孩子,是个好兵。”
06
我们在会客室里,聊了很久。
孔繁军向我详细询问了我在部队的生活,以及家里的情况。
他的语气,就像一个邻家的长辈,亲切又温和,完全没有了刚才的严肃。
我拘谨地回答着,心里却依旧波澜起伏。
我怎么也想不到,那段已经快要被我遗忘的经历,背后竟然藏着这样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。
“霄然,转业了,有什么打算吗?”孔繁军问。
“还没想好,可能……进矿上找个活干吧。”我老实回答。
“烧锅炉?或者当个保安?”孔繁军笑了笑,“你这样在部队里锻炼出来的优秀人才,就这么埋没了,太可惜了。”
我苦笑了一下,没有说话。
我们这种没学历、没背景的农村兵,除了力气,一无所有,不干这个,又能干什么呢?
“我这里,有个想法,想听听你的意见。”孔繁军说。
“首长您请讲。”
“清雪,也就是张诺伊,她回到内地后,并没有待在总院。”孔繁军的眼神变得柔和起来,“她用我们给她的补偿金,加上她自己的积蓄,在西南山区,创办了一个小型的医疗救助站。”
“那个地方,比你们之前的驻地条件还要艰苦,交通不便,缺医少药。她一个人,既是医生,也是护士,还是院长。”
“她现在,最缺的,就是一个能帮她管理后勤,处理杂务,最重要的是,能让她信得过的人。”
孔繁军看着我,目光灼灼。
“霄然,我知道,这个请求很冒昧,也很自私。你刚刚才脱下军装,回到家人身边,我本不该再来打扰你。但是,除了你,我实在想不出更合适的人选了。”
“那个地方很苦,工资待遇,肯定比不上你在矿上。甚至,还有一定的危险性。”
“但是,我觉得,那份事业,是有意义的。你,愿意去帮帮她吗?也算是,帮我这个老头子一个忙。”
我没有立刻回答。
我的脑海里,浮现出李娟那张现实的脸,浮现出我妈期盼的眼神,浮现出那座小城里日复一日的煤烟味。
然后,又浮现出张诺伊那张在风雪里倔强的脸,浮现出她清澈明亮的眼睛。
一边,是看得见的安稳生活。
另一边,是未知的艰苦和挑战,但那里,有我曾经向往和守护过的东西。
我几乎没有犹豫。
我站起身,对着孔繁军,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“首长,我愿意去!”
07
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家里人时,毫无意外地,掀起了轩然大波。
“啥?你去西南山区?给人当什么管理员?你疯了!”我妈的嗓门一下子就提了起来。
“霄然,你是不是脑子让驴踢了!”我爸把手里的酒杯重重地墩在桌子上,“放着矿上办公室主任的女婿不当,跑去那鸟不拉屎的地方受苦?你图啥啊!”
“图啥?就图那是个有意义的事!”我忍不住跟他们吵了起来。
那是我长这么大,第一次跟我爸妈红脸。
“有意义能当饭吃?能换来钱?”我爸气得浑身发抖。
“爸,有些东西,比钱重要。”
“你……”
那天晚上,我们家吵得不可开交。
我妈坐在炕上,一个劲儿地抹眼泪,说她白养了我这个儿子。
我爸指着我的鼻子,骂我是个不孝子,是个傻子。
我知道,他们无法理解我的选择。
在他们的世界里,安稳地过日子,娶妻生子,就是最大的人生幸福。
而我,却要去选择一条在他们看来,又苦又没有前途的路。
第二天,我没有跟他们告别,只是默默地收拾好行李。
我把大部分转业金都留在了家里,只带了很少一部分。
临走前,我给他们磕了一个头。
当我背着行李包,再次站在村口时,我的心情,和回来时已经完全不同。
没有迷茫,也没有不舍。
我的心里,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坚定。
我知道,我不是在逃离,而是在奔赴。
奔赴我的另一个战场。
孔繁军给了我地址和联系方式。
我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,又换乘了长途汽车,最后,搭着一辆运送物资的拖拉机,才终于抵达了那个叫“云川”的地方。
这里,比我想象的还要偏僻。
群山环绕,道路崎岖。
所谓的救助站,就是几间用石棉瓦搭建的简陋平房,墙上用红漆写着“云川乡医疗救助站”几个大字。
我到的时候,正是中午。
一个穿着白大褂的身影,正在院子里给一群孩子分发糖果。
阳光照在她的身上,让她整个人都像是在发光。
她听见拖拉机的声音,回过头来。
四目相对。
是张诺伊,不,是孔清雪。
她瘦了,也黑了,但那双眼睛,还是那么亮。
她看到我,先是愣了一下,随即,脸上露出了一个灿烂的,发自内心的笑容。
“你来了。”她说。
“我来了。”我回答。
没有多余的话,但我们都懂。
08
我在云川乡安顿了下来。
我的工作,就像孔繁军说的那样,繁杂而琐碎。
采购物资,维修设备,管理账目,有时候还要充当司机和保安。
救助站除了孔清雪,只有一个本地的姑娘当助手,我们三个人,就是这个小站的全部班底。
这里的日子的确很苦。
我们经常要面对停水停电,物资短缺的困境。
我开着那辆破旧的吉普车,在盘山公路上来回奔波,好几次都差点连人带车翻下悬崖。
但我的心,却是前所未有的踏实。
每天,我都能看到孔清雪为了救治病人而忙碌的身影。
她会因为抢救回一个难产的孕妇而露出疲惫的笑容,也会因为无力挽救一个重病的老人而偷偷地掉眼泪。
她把所有的热情和精力,都投入到了这片贫瘠的土地上。
她就像一棵格桑花,在最艰苦的地方,开出了最美的花。
我们之间,没有儿女情长。
我们是战友,是同志,是在同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伙伴。
她叫我“林管理员”,我叫她“孔医生”。
我们之间,保持着一种默契的距离,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。
我知道,她心里装着的,是这片大山,是这里的百姓。
而我,只要能为她守好后方,让她能安心地去实现她的理想,就足够了。
一年后,孔繁军来看过我们一次。
他看到救助站井井有条,看到山里的百姓提起孔清雪都竖起大拇指,他很欣慰。
临走时,他把我拉到一边。
“霄然,委屈你了。”他说。
我摇了摇头:“首长,我不委屈。能参与到这么有意义的事情里,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光荣。”
孔繁军拍了拍我的肩膀,什么也没说,但他的眼睛里,是深深的感激。
日子就在这平淡又忙碌中一天天过去。
救助站的条件,在一点点地改善。
我们有了新的发电机,有了更齐全的医疗设备,甚至还争取到了一批志愿者的支持。
孔清雪的脸上,笑容也越来越多了。
又是一年冬天。
山里下起了大雪,封了路。
救助站里,烧着温暖的炉火。
我们三个人,围坐在一起,吃着热腾腾的火锅。
窗外,是漫天的风雪。
窗内,是温暖的灯光和家的味道。
孔清雪看着窗外,忽然轻声说:“又下雪了,真像那年啊。”
我知道,她说的是我们相遇的那年。
“是啊。”我点了点头,“不过今年的雪,看起来,很暖和。”
她转过头,看着我,笑了。
那笑容,像冬日里的暖阳,瞬间融化了所有的冰雪。
我知道,我找到了我的哨位。
我的余生,就是要站在这里,为她,也为这片大山,守护这一方光明。
短线配资平台,配资公司官网,实盘配资公司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南京开户配资在二季度均新进增持三生制药
- 下一篇:没有了